专访朱丹教授:聚焦肝脏核心作用!看心肝肾代谢综合征如何突破传统框架,为疾病干预提供新方向
时间:2025-09-25 15:40:57 热度:37.1℃ 作者:网络
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,肥胖、高血压、高血糖、血脂异常等代谢紊乱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呈爆发式增长,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挑战。过去,临床上通过“代谢综合征”这一概念来整合评估并存的危险因素。然而,随着研究的深入,科学家们逐渐认识到,这种将各项指标简单并列的模式,难以完全解释临床中多器官功能进行性损害的复杂关联。
在此背景下,代谢综合征正从“单项指标管理”向“器官网络联动”的整体观转变。在2025年第四届中国肥胖大会(COC)上,梅斯医学特邀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朱丹教授,系统阐述了“心肝肾代谢综合征”这一新兴理念,揭示了其如何突破传统框架,将肝脏置于核心枢纽地位,阐释心、肝、肾等器官在代谢压力下相互影响、共同进展的内在机制,为代谢性疾病的早期识别、风险评估和综合干预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与方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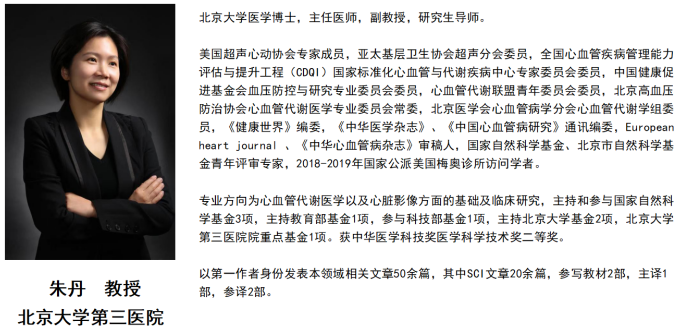
梅斯医学:心肝肾代谢综合征作为涉及心脏、肝脏、肾脏及代谢系统的交叉病症,其核心病理机制与传统代谢综合征相比有哪些独特之处?
朱丹教授:心肝肾代谢综合征并非仅仅是传统代谢综合征的简单重复,而是一个更深入、更全面的“升级版”,两者在多个层面存在核心区别。首先,在对脂肪的关注点上,传统代谢综合征主要通过BMI值和腰围来衡量内脏脂肪的累积,但并未深入关注脂肪的具体分布,而心肝肾代谢综合征则更加强调对脂肪沉积的定位,特别是肝脏脂肪的沉积及其带来的深远影响。内脏脂肪释放的游离脂肪酸涌入肝脏,诱发代谢相关脂肪肝病(MASLD),进而触发"脂毒性循环":肝脏从被动的代谢器官转变为主动的"内分泌器官",释放肝源性因子(如胎球蛋白-A、FGF21)和炎症因子(IL-6、TNF-α),这些因子通过血液循环直达心脏和肾脏,直接损伤血管内皮和心肌细胞。
其次,在器官关系的理解上,代谢综合征倾向于将高血压、高血糖、血脂异常等问题并行看待,而心肝肾代谢综合征则认为心脏、肝脏、肾脏等器官之间存在着串联的、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,CRHM揭示了肝心双向互作的恶性循环:肝→心损伤通路:肝脂毒性导致心肌细胞内脂质沉积,抑制心肌收缩力;肝源性IL-6激活心肌STAT3通路,加速心肌纤维化;
心→肝反噬通路:心功能不全影响肝脏灌注;心脏分泌的ANP异常调控肝糖脂代谢,形成一个逐级放大的恶性循环。最后,在对肝脏角色的认知上,心肝肾代谢综合征将其提升到了极其重要的地位,不仅视其为代谢器官,更强调其作为内分泌器官的作用,能分泌白介素-6等因子主动影响心血管系统。
当然,心肝肾代谢综合征还有一个重要新启示,肝脏纤维化和心脏纤维化共享相似的病理过程, TGF-β/Smad通路在肝星状细胞和心肌成纤维细胞中同步激活,CTGF过度表达促进肝内胶原沉积和心肌间质纤维化。因此一个器官的纤维化程度可以预测另一个器官的疾病进展,临床数据显示,F2期肝纤维化使心衰风险增加2.5倍,F3-F4期风险达3.42倍。这一发现为疾病的早期预警提供了重要依据。
梅斯医学:目前,针对心肝肾代谢综合征是否已经形成了统一的诊断标准?是否有必要建立独立的诊断框架,以区别于传统代谢综合征?
朱丹教授:对于如何识别心肝肾代谢综合征,我们建议从基础测量入手:男性腰围≥90厘米、女性≥85厘米提示内脏脂肪过多;诊室血压≥140/90 mmHg或家庭自测≥130/85 mmHg需警惕高血压;空腹血糖≥6.1 mmol/L、餐后2小时血糖≥7.8 mmol/L提示血糖异常,餐前低血糖发作、餐后犯困严重、莫名口渴、皮肤伤口愈合慢提示筛查血糖的必要;甘油三酯≥1.7 mmol/L、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(HDL-C)男性<1.04 mmol/L、女性<1.3 mmol/L则为血脂问题。此外,一些易被忽视的症状也需注意,如休息后仍无法缓解的疲劳、不明原因的水肿或皮肤发黑,这些都应及时就医确诊。
梅斯医学:在临床实践中,针对心肝肾代谢综合征这一新兴概念,您认为应如何在早期阶段实现精准识别?在干预方面,有哪些基于循证医学的综合管理策略可以有效改善患者预后?
朱丹教授:心肝肾代谢综合征治疗方案主要为生活方式调整和药物治疗。生活方式调整包括采用低糖、低脂、低盐饮食,并用粗粮替代精细米面以改善胰岛素抵抗,同时坚持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运动。药物治疗方面,新型降糖药如SGLT-2抑制剂和GLP-1受体激动剂不仅能降糖,还能减轻内脏脂肪、肝脏脂肪并改善心血管预后。针对肝功能的药物如水飞蓟宾、甘草酸类或FXR激动剂也可辅助使用。对于BMI≥32.5的严重肥胖患者,代谢手术是有效的选择,能显著减轻体重并全面改善代谢状况。
总之,“心肝肾代谢综合征”标志着对传统“代谢综合征”认知的深化与升级,其核心在于突破了对代谢异常的孤立看待,强调器官间的串联互动与共同病理基础,尤其聚焦肝脏脂肪沉积,将肝脏重新定义为驱动多器官损害的主动内分泌参与者,并揭示了肝心纤维化进程相互预测的内在联系;这一整合视角为临床提供了更清晰的早期识别路径(结合腰围、血压、血糖、血脂及疲劳、水肿等症状),并推动治疗策略转向以生活方式干预为基石,结合SGLT-2抑制剂、GLP-1受体激动剂等多效药物及代谢手术的综合管理模式。


